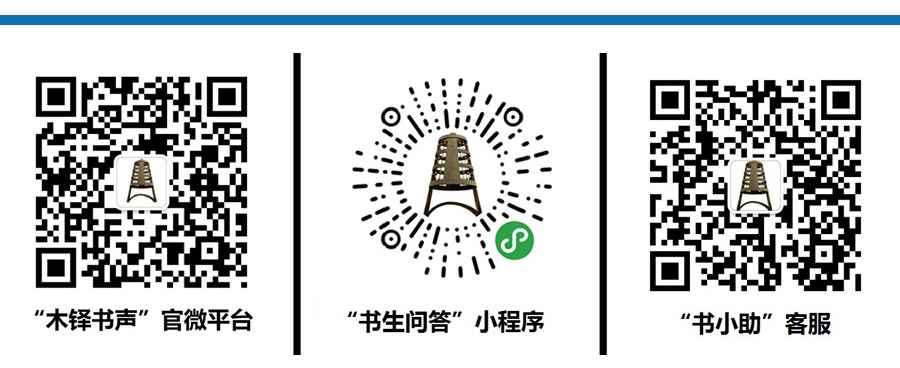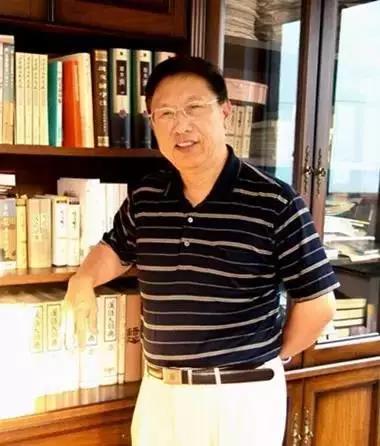
郝铭鉴 著名语言学家 《咬文嚼字》杂志原主编
一个普通的“袭”字,却让我感到像石头一般沉重。
朋友问我:你说“袭”字用作量词,只能用于服装,“一袭礼服”是对的,“一袭长发”则是错的。这是为什么呢?而且说只能用于成套服装或长形服装,“一袭长衫”是对的,“一袭短袄”则是错的。这又是为什么呢?
是的,话是我说的。但我不是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回答不了这一个接一个的问题。当时脑子里倒是闪了一下:“袭”字是由“龙衣”构成的。龙衣者,皇袍也。你没见过袍子吗?由袍子引申出来的量词,对适用对象有所限制,有什么可奇怪的?
回家后便查《说文》。天呀,幸亏“皇袍”没说出口,原来“袭”指死者穿的衣服!它还有一种写法“ ”,上面是两个“龍”字。请看《说文》:“襲,左衽袍。从衣,龖(dá)省声。
”,上面是两个“龍”字。请看《说文》:“襲,左衽袍。从衣,龖(dá)省声。 ,籀文襲不省。”
,籀文襲不省。”
右开襟是活人穿的,左开襟是死人穿的。可是——这时我自己脑子里出现了问号:难道因为死者穿的是成套殓服,“袭”字便限用于成套服装或长形服装吗?多么古怪的思路!
于是再查《汉语大字典》,一个个义项扑面而来:死者穿的衣服、重衣即衣上加衣、重叠、因袭、继承、袭击……它丰富了我对“袭”字的认识,却又增加了我心头的困惑。
我一直认为,汉字是有大智慧的,造字必有理据,用字必有逻辑;即使只是声符,也未必和意义没有联系。可“龍”或“龖”和死者的衣服何干?死者静静地躺着,“袭击”义又从何而来?这些跨度甚大的义项,让我有点眼花缭乱。
于是又查《古文字诂林》。这是一部大型工具书,它汇录了历代名家关于古文字形音义的考释成果。以往遇到难题,总能从中得到启发,这次似乎不太走运。
书中有一条倒是说得挺详细的:“卜辞又作祖先名,以声类求之,当为契。”“金文也有这个字,可能是绣有龙纹的民族服装,本意是一种衣服的名称。”它“至少兼并了甲骨文表示‘偷袭’和‘重衣’的两个古文字”。信息量不可谓不大,其中“绣有龙纹”四字,让我眼前一亮;可仔细一琢磨,前面的“可能是”三字,又让我心头一沉。我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。
人就是这样,越是回答不了,越想探个究竟,以至到了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境界。
一天早上起床,脑子里突然冒出一条成语:“龙蛇之蛰”。它出自《易经·系辞下》:“龙蛇之蛰,以存身也。”施蛰存先生的大名便典出于此。龙蛇,通常的解释是巨龙长蛇,这一解释似乎还可斟酌。在《易经》中,它是和“尺蠖”对应的,应该只是一种动物;而且,冬眠也只是蛇的习性。我认为“龙蛇”即像龙一样的蛇,犹如“龙马”即像龙一样的马。我们家乡属蛇的人,在回答别人提问时,往往会说自己是“属小龙的”,以龙代蛇。“袭”字上面的“龙”,莫不就是蛇吧?这个念头一出来,顿时有隧道走到尽头的感觉。我想,所谓“龙衣”或许就是蛇蜕呀。
怪不得“袭”字的写法,可以是两个“龙”字。两条龙其实是一条龙。一条是蜕变前的蛇,一条是蜕变后的蛇。一条蛇蜕变后留下“龙衣”,成了另一条蛇,但它的生命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。于是,“袭”有了继承的意思。因袭、承袭、世袭包括抄袭,都和继承有关。“袭击”呢?我小时候住在农村,经常看到草丛里的蛇蜕,却从未见过正在蜕皮的蛇。蛇的蜕皮是具有隐蔽性的,所以用作动词时,总有偷偷的、悄悄的色彩,如夜袭、突袭、奔袭、奇袭。
慢着,有一个关键问题:为什么古人众口一辞地把“袭”说成是死者穿的衣服呢?呵呵,这个可以解释:先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,人死后灵魂飞升,留下的只是躯壳。这和蛇的蜕变有相似之处。而按照古代的习俗,死者的殓服既有常衣,又有袭衣,多层包裹,由此自然又会引申出重衣、重叠等义项。
想到这里,不禁长呼了一口气。我觉得可以回答朋友的问题了。见过蛇蜕的人都知道,蛇蜕下的皮是完整的、长形的。因为有这样一个常识背景,人们把“袭”用作量词时,下意识地用于成套服装或长形服装,久而久之,成了共同遵守的规范。
造字必有理据,用字必有逻辑。“袭”字并不例外。